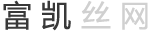夜是张伟豪的战场,他说自己是见月亮最多的人,所以把月字放进店名里。但他没时刻昂首赏识月色,更多时分是在静心烤串。
“要吃啥子嘛?”一个穿戴淡蓝色T恤的年青男人走到张伟豪的烧烤摊前,盯着冰箱里的烤串,张伟豪微笑着问他。
黄昏六点半,天色未暗,来吃夜宵的人还不多。男人从冰柜里取出两串羊肉串,两串骨肉相连,一串鸡翅,一串土豆片,一串豆角,两串小瓜。张伟豪递给他一个白色镂空的塑料篮子,让他把烤串都装在里边。
招待客人坐下后,张伟豪从篮子里取出烤串,再一串串平铺在提早预热好的烤架上,几分钟后,肉串宣布滋滋的声响,烤架上飘起一缕缕青烟。
张伟豪眯着眼,烟熏得他皱起眉,给肉串翻了个身,又从周围桌子上相继取出一瓶胡椒粉,盐巴,辣椒粉,右手一边抖一边撒在烤串上。
“老板,来个炒饭噻!”烤串还没好,又有客人喊道。张伟豪让自己招的杂工过来盯着烤串,他快速站到另一边的炒饭锅灶前。打火,上锅,下油,铲起一勺白米饭下锅,一只手搅,一手掂锅,米粒飞到空中,又下跌锅底。接着,他又相继把各种调料加进去,最终撒上葱花和切丁泡菜,满满一碗,端到客人桌前。

张伟豪穿一件白色短袖T恤,胸前挂着黑色围兜,上面印着“抓住搞钱”四个白字。
“妹儿,勒边坐!”他一边拧开一盏白炽灯,一边招待刚过来的客人。他的货摊主打的是泡椒脑花,锡纸鲫鱼,蒜蓉粉丝茄子,网红把把烧,功夫炒饭等。整条夜市街上,和他相同的烧烤摊主最多。
“老板,结账,算一哈嘛!”有客人等不及,敦促张伟豪。他从烧烤摊转到炒饭摊,又从炒饭摊转到餐桌周围,来来,他的脸越来越红,额头上冒着汗。
夜幕降临,笼罩着张伟豪的烧烤摊。其他夜市摊主陆连续续点亮了霓虹灯牌,紫色,赤色,绿色的灯火连成一片,映照着城市的夜空。夜空变成五颜六色,渗进薄薄的雾气里,掩盖在城市的街道上,掩盖在来交游往的行人身上。
在鲜香麻辣的重庆,夜市是一张手刺。它的贩子烟火气,从不回绝任何人,也包容了这座城市和人的夜晚心思。

重庆是山城,地形凹凸崎岖。张伟豪的烧烤摊紧挨着马路,坐落在一个有点歪斜的坡坝上,十张矮脚方桌规整摆放在周围一块罕见的平地上,桌子上铺着黑白相间的千格鸟桌布,每张桌子配四张橙色塑胶靠背椅。
依照办理规则,夜市一般从黄昏六点开端,继续到清晨三点。但摊主们会在下午五点左右,从家里连续搬出烧烤架,锅具碗具,食材,桌椅等,全部准备作业安排妥当,一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张伟豪本年27岁,在夜市摊做了5年生意。从技校毕业时,他进了一个汽修厂打钉子,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。那时每月薪酬一千多,不行他开支,“耍朋友(谈恋爱)都不行哦。”他回忆说。
所以,姐姐让他到自己的烧烤摊帮助,每月给他开四五千的薪酬。张伟豪不惜力,干活很拼。后来姐姐在其他商场开了小吃店,就把这个夜市货摊转给了他。
张伟豪记住,疫情前,吃夜宵的人许多,生意最旺时,他还招了三个杂工,每月发给他们每人三千的薪酬。后来,客流显着少了,他常常坐在椅子上发愣,看交游的行人和车流。即使如此,他仍是会出来摆摊,究竟 “能挣一点是一点。”
张伟豪不是重庆市里的人,他的家在离重庆主城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垫江。由于要摆夜市摊,他在邻近租了一间房子,每月租金一千多,加上几百元的货摊费,有时会让他感受到日子在城市的压力。
这些年,重庆成了网红城市,张伟豪也听过许多网红景点,比方穿楼而过的轻轨,夜里灯光璀璨的洪崖洞,长江索道。但他白日要补觉,晚上要出摊,就没有消遣的时刻。
比起去抢手景点,张伟豪更美观夜市里的日子,那里是他能掌控的领地。在他眼里,烤好一串烧烤大有学识,“不能太焦,不能太绵,不能不新鲜,不比他在工厂打钉子简略”。
防疫铺开至今,张伟豪感觉客流还没有神出鬼没到早年的水平。但他深信生意会渐渐的好。
客人较少时,夜市摊主们会串门谈天。张伟豪的“街坊”是一对年青的“90后”配偶,他们的货摊面积比张伟豪的小一半,货摊租金也廉价一半,只卖些简略的凉面,冰粉,糯米凉虾,面条抄手。

夫妻俩原本在重庆服装商场有一家店,但疫情期间生意欠好,关闭了。老公开端跑网约车,白日接单,晚上就和妻子一块儿出来摆夜市。他们有一个三岁的儿子,平常是爸爸妈妈带,但现在爸爸妈妈身体欠好,他们就把孩子带到了夜市。
夫妻俩繁忙起来时,一个盯着锅里的抄手,一个拌着手里的凉粉,孩子趁爸爸妈妈不注意,跌跌撞撞跑进了张伟豪的烧烤摊里。
孩子顽皮,把手伸进张伟豪洗净的青菜里,拿起一颗四处挥舞。张伟豪看着他,笑嘻嘻的。孩子没站稳,膝盖着地扑下去,哇哇哭起来,张伟豪急速放下手里的锅铲,把孩子抱起来,又给他一颗煮熟的鹌鹑蛋。孩子止住哭声,就跑回爸爸妈妈身边了。
晚上七点多,不忙的时分,张伟豪把一大锅海带排骨汤端到桌子上,加上一碟空心菜,一盘青椒肉丝,盛好米饭,往街坊的货摊走去。过了会儿,街坊夫妻牵着儿子来到他的饭桌前,几个人围坐在一起,边聊边吃起来。
“那必定噻,我自己弄的。”张伟豪笑着说,夹起一块排骨浸入蘸料碗里,扔进嘴里大口嚼起来。
说完,他几筷子刨光碗里的饭,又动身走到烧烤摊前,掏了掏里边的木炭。木炭表层的灰掉下去,显露橙红的火光,映红了张伟豪的脸。
在这个夜市,张伟豪见过形形的人。有人只点一个菜,几瓶酒,发愣,一向坐到清晨三点才脱离。还有朋友集会的,有时是年青人,有时是中年人。一些人不美观去花天酒地的酒吧,反而更美观接地气的街边夜市。几个人围在一张矮桌前,你一筷子我一筷子,大声谈天,嬉笑怒骂,人们的声响交错在一起,飘扬在街上,“夜晚好像没那么孤单了”。他用抹布擦了擦手,又回身走到烤箱前。

有时也有外地人,乃至外国人来考烧烤吃,张伟豪在方言和不规范的普通话之间切换,但他不会英语,只能手舞足蹈地比画。
依据他的调查,来吃烧烤的,有深夜下班的,也有深夜睡不着的,还有肚子被饿醒的、嘴馋的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。
一个冬季夜里,清晨两点左右,一个女孩穿戴单薄的睡衣跑到他的烧烤摊前,哭着说要10瓶啤酒。女孩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,头发乱糟糟的,睡衣也没扣好,穿戴一双拖鞋。
张伟豪看着不对劲儿,就说要不你先喝一瓶吧,喝完再拿。女孩不同意。他只能取出10瓶啤酒拿给她。
女孩坐在桌前,一边哭一边喝。张伟豪猜想她是遇到了感情上的问题,但他不敢多问。我行我素一边留心女孩的状况,一边招待其他客人。女孩喝完6瓶啤酒后,没怎么哭了,也没醉,付完钱就脱离了。
在夜市,张伟豪最怕遇到喝酒捣乱的人,酒意正酣,劝不住。但幸亏这样的作业很少遇到。这份日夜倒置的作业赚的是辛苦钱。之前,张伟豪招了一个杂工,干了不到一个星期,就喊腰酸背痛,还摔破了两个碗,张伟豪发给他一个月工钱,让他脱离了。
张伟豪在乡村出世长大,很小时就跟着爸爸妈妈去地里干农活。他习惯了起早贪黑,比起在工厂打钉子,他更美观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他说,趁自己年青,多干点儿活。
夜里,客人吃完连续走后,留下满桌空碟,空酒瓶。张伟豪敏捷把它们捡走,生菜倒进垃圾桶,再用抹布把桌子擦洁净,迎候新客人。
他说,拾掇速度必定要快,要洁净。不论多晚,只需没收摊,新的客人就会来。回来搜狐,检查更加多